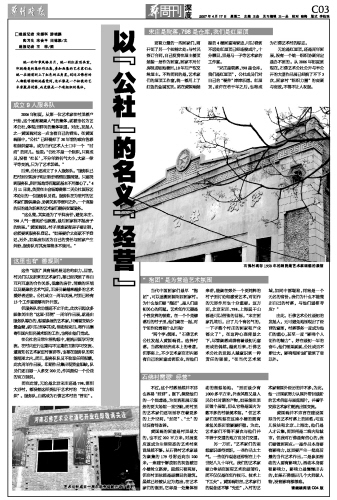|
 |
|
|
|
||||
| 以“公社”的名义“经营” 中原网 日期: 2007-04-17 来源: 郑州晚报 |
成立9人服务队 2006年初夏,从第一位艺术家在村里落户开始,这个逐渐凝聚人气的集体,就被命名为艺术公社,体现出鲜明的集体味道。对此,发起人之一黄国瑞对这一点也有自己的看法。在黄国瑞眼中,“公社”已经褪掉了30年前的政治色彩和组织意味,成为当代艺术人士口中一个“时尚”的词儿。他说:“公社不是一个组织,只有成员,没有‘社长’,不分年龄名气大小,大家一律平等交流,只为了艺术切磋。” 后来,公社还成立了9人服务队。“服务队已把村里空闲房子和出租价格情况摸清楚,只要找到服务队,租用场地等问题就基本不用操心了。”4月11日晚,负责在主会场筹备第二天公社国际艺术论坛的一位服务队员说,服务队在为驻村的艺术家们提供聚会、协调关系等便利之外,一个直接的目的是为新来的艺术家们提供安置服务。 “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平抑房价,避免宋庄、798人气一涨地价也疯涨,最后画家租不起房子的结果。”黄国瑞说。村子里谁家有房子要出租,必须要到服务队登记。“如果要价太高就不予登记,另外,如果房东因为自己的责任与画家产生纠纷,服务队对其房屋将永不续用。” 这里也有“潜规则” 这些“规矩”具有显而易见的约束力。目前,村民们以及新来的艺术家们,都已经找到了各自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低廉的房价、清幽的环境以及凝聚的艺术气质,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艺术爱好者进驻。公社成立一周年庆展,村里已经有13个工作室能够对外开放。 但服务队的功能还不止于此,此次引起众多媒体关注的“这屋·那院”一周年作品展,就是由服务队筹办的,想要参展的艺术家,只需要交纳少量金额,就可以坐享其成,活动结束后,将作品集寄往国内知名美术馆的工作,也将由他们完成。 在公社的日常生活构想中,轮流出国学习交流、在村内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互相学习交流、邀请知名艺术家进村演讲等,也都在服务队的职能范围之内。而且,服务队队员不收取任何报酬,此次周年作品展,印刷作品集出现资金短缺,队员们还自愿一人多交200元,作风颇似一个公益的官方组织。 而在此前,无论是北京宋庄还是798、深圳大芬村,都没有这样类似于艺术村的“官方组织”。服务队,自然成为石佛艺术村的“首创”。 宋庄是院落,798是仓库,我们是红屋顶 更有力量的一些画家们,则开创了另一个独特之处:与村民签订合同,自己投资在屋主楼顶续接一层作为画室,画家不用付房租或场地费用,10年后产权交给屋主。不约而同的是,艺术家们的屋顶工作室,统一都用上了红色的金属瓦顶。站在黄国瑞续接的4楼画室南窗边,可以看到不远处红屋顶已经连接成片,十分醒目,那是马一子等艺术家的工作室。 “宋庄是院落,798是仓库,我们是红屋顶”,公社成员们对自己的“硬件”津津乐道。红屋顶,或许在若干年之后,也将成为石佛艺术村的标志。 无论是红屋顶,还是周年画展,没有一个统一组织协调肯定是办不到的。从2006年初夏到现在,石佛艺术公社公开与半公开的大型作品展已经搞了不下3次,画家村“组织力量”的高调与高效,不得不让人叹服。 “抱团”是为营造艺术氛围 当代中国画家们最早“抱团”,可以追溯到圆明园画家村。为什么他们要“抱团”,是人们最初关心的问题。艺术创作无疑是个性发挥的极致,在一个个荒僻落后的村子里,他们聚在一起,对于创作究竟有什么用呢? “两个字:氛围。”石佛艺术公社发起人黄国瑞说。选择村落,当然有经济成本上的考虑,但事实上,不少艺术家在市内都有自己的画室或者职业,对他们来讲,能聚在郊外一个更纯粹的村子里讨论和感受艺术,对创作的无形作用也十分重要。这方面,北京宋庄、798、上海莫干山都是可以借鉴的目标,“宋庄画家扎堆后,出了几个有名气的,一下子整个村庄的画家和产业都火了”,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尽管聚落成群有着最初无意而成的偶然,越到后来,石佛艺术公社的发起人越意识到一种责任的驱使,“在当代艺术领域,如同中部塌陷,河南是一个无名的省份。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自己的村落,与他们遥相呼应?” 由此,石佛艺术公社最初的发起人,无可避免地显现出了经营的意图,村落事务一度成为他们的重心,甚至一度“影响个人创作的精力”。好在最初一年的奋斗,他们硕果累累,公社成员不断壮大,影响范围也扩散到了省以外。 石佛村需要“经营” 不过,这个村落显然并不那么容易“经营”。眼下,缠绕他们的一个焦虑是,为交流和展示服务的更大场馆一直空缺,而村里的艺术家们还明显存在着更多的上升空间,“封闭”、“土”的状况有待改善。 黄国瑞的画室是村里最大的,也不过202平方米,对展览应该成为生活常态的艺术村来说显然不够。从石佛村艺术家最为聚集的179号附近向东200米,一座建于解放初的灰色破旧小楼耸立路旁,虽然只有两层,但在村里依然是最醒目的建筑。虽然已经被认定为危房,在艺术家们的眼里,它却是一处集体活动的理想场地。“里面最少有1000多平方米,外表风格又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如果能在里面做个展馆,那么它将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村级美术馆。”但艺术家们的构想在这座小楼的既有承包关系面前屡屡折壁。为此,艺术家们不得不屡次与他们并不善于交道的地方官员们交道。 另一方面,“艺术家们的思想意识亟待更新,一些作品太土气,一些创作观念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艺术家要力争站在国际艺术的最前沿,而不仅仅是在创作技巧、技术上下工夫”。黄国瑞坦言,艺术家们的观念还不够“先进”,入村的艺术家有国外经历的并不多,为此,他一出国就努力从国外带回最新的艺术信息与展览照片,并着手安排艺术家们轮流出国交流。 黄国瑞并不讳言在建设国际当代艺术村落上的困难:咱这儿没法和北京、上海比,他们是人才云集,而郑州是二线内陆城市,但我对石佛是有信心的,我们要做到两点:一是作品本身要有影响力,这里要产生一批高质量的当代艺术作品,二是参加活动的人要有影响力,活动本身要有影响力,影响力是慢慢出去的,如果石佛能出几个大师级人物,没有影响都很难。 请继续阅读C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