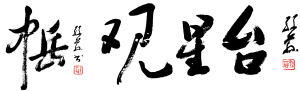名家新篇
陈子善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是鲁迅的名言,是鲁迅晚年在其名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的话,掷地可作金石声。1986年秋,在浙江宁波巴人学术研讨会上,我请黄源老为我书写一小笺,他想了一想,写下了鲁迅这句话。这可以看作作为鲁迅学生的黄源老对鲁迅的敬重,也可以看作黄源老晚年借鲁迅的话以自况,显示了他对新知的追求。
我第一次见到黄源老是1978年春天,那一天是阴天。沿西湖湖滨路走到他在葛岭上的寓所,要爬很长的台阶,走得又很急,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很累很热,满头大汗。只记得当时室内光线比较暗,但黄源老的热情,顿使我感到很清凉,很亮堂。对于这位文坛前辈来说,我只是一个小伙子,也是一个不速之客,可是他没有架子,耐心地解答我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许多问题。
黄源老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也在1986年秋的巴人研讨会上。我们一起到巴人墓地祭拜,黄源老忽然号啕大哭,虽然黄源老是中共党内的一个高级文化干部,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文人,一个性情中人。黄源老除了鲁迅以外,谈郁达夫谈得很多,曾应我之请写了《在<蜃楼>描绘的葛岭追念前辈郁达夫》,正是因为他和郁达夫一样,都是性情中人,真诚的人,他推崇郁达夫的真诚。
如何给黄源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定位?他是一个鲁迅研究家,他既然写了那么多研究鲁迅的文章,出版了《纪念鲁迅》、《在鲁迅身边》、《鲁迅致黄源信手迹及注释》等书,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弘扬鲁迅精神他是不遗余力的,所以称他为鲁迅研究家,他是当之无愧,毫无疑义的。从《黄源文集》第一卷、第二卷可以看到,他也是一个散文家,有他自己的散文风格,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风格。《黄源文集》第三卷是译文集,再清楚不过,他又是一个翻译家,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到晚年,他都在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不少东西方的优秀文学作品。
除了鲁迅研究家,除了散文家、翻译家,黄源老还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家。然而,文学编辑家的黄源老至今没有引起研究界足够的重视。黄源老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杂志和《译文》杂志的编辑。我们往往对文学编辑家在文学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不仅仅是忽视了黄源老。没有他们多姿多彩的文学编辑活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进程就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文学》是在《小说月报》停刊以后,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小说月报》传统的极为重要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杂志,我们对《文学》的总体评价过低,当时大型的文学杂志除了《现代》就是《文学》。《文学》的具体编辑工作就是黄源老在做,很多史料值得进一步发掘,进一步思考,进一步探讨。后来,他又接手鲁迅、茅盾、黎烈文创办的《译文》的编辑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这是一个专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早期的新文学作家,像鲁迅、茅盾、郁达夫、巴金他们,本身的外文水平都很高,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许多人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热爱文学,他们需要好的精神食粮,渴望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以资借鉴。《译文》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为文学青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所以黄源老这个文学编辑家的身份应该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好好地研究讨论。
我三年前在杭州一家小旧书店觅到一本已故唐振常先生著《蔡元培传》(1985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这是黄源老的藏书,扉页上有黄源老的红笔题字:“一代巨人 黄源 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日”。边上又有较小的黑笔题字:“二月五日至八日夜读完”。黄源老当时已八十九岁高龄了,但读《蔡元培传》仍读得很仔细,很用心。红杠蓝杠画了很多,书中写到“元培之‘大’,核心就在于他的兼容并包”,黄源老在这句话下画了红线,在“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下面也画了红线。每读完一章黄源老又要记下具体时间。如第七章末就有红笔所书:“1993年2月6日,散步回来,上午十一时”。凡书中写到鲁迅的地方,也都一一着重标出,加上按语。这本批注本,见证了黄源老晚年的好学不倦,是他实践“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的一个极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