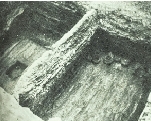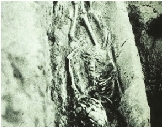|
 |
|
|
|
||
|
|||||||||||||||
在陕西西安市南郊的一栋普通居民楼内,住着一位年过半百的考古学者,他叫卢连成。如今的卢先生已远离了艰辛的野外考古,过着悠闲而平淡的日子,但不经意间,他还会常常忆起3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75年,在距离宝鸡市百十来里远的一个叫茹家庄的黄土台塬上,一座西周时代的古墓惊现在人们眼前,这是一个悬疑密布的墓葬:几件简单的工具、深埋黄土中的凌乱人骨、精美的青铜器,使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古国若隐若现,而卢连成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考古人员…… 古国初显 1975年,在宝鸡市茹家庄的黄土台塬上,村民们日复一日地平整土地,修筑梯田,一天,村长杨列无意中刨到了一个土坑…… 随着挥舞的锄头落地,迸出了清脆的响声,杨列弯腰察看,发现了一块古怪的铜疙瘩。 他用手扒拉掉泥土,发现这块铜疙瘩非同一般,上面居然镂刻着细密的花纹。 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宝鸡市文管所的所长李仲操当即派遣大学毕业不久的卢连成前往茹家庄。 卢连成捡起那些铜疙瘩,根据考古常识,这些绿锈斑驳的铜疙瘩显然是小型的青铜构件。 茹家庄是西周遗存和墓葬分布密集的地区,而青铜构件又是比较典型的西周器物,卢连成判断,他们的脚底下极有可能埋藏着西周时期的遗存。但他并没意识到,这些青铜构件仅是冰山一角,一个史籍失载的古国即将显露。 发现墓室 考古发掘工作随后紧锣密鼓地展开,手铲开始叩开远古时代的遗迹。 卢连成首先清理出车轮印痕。紧接着,在手铲的拨弄下,一些骨头逐渐露出泥土,这些泛黄的骨头从外观看来不像人骨,而是某种动物的骨骼,而后,愈来愈多的骨头大体能拼凑出马的骨架。加上先前的车轮印痕,卢连成基本断定,目前清理的是一座陪葬车马坑。 就在此时,令人诧异的情况出现了: 在编号为茹家庄1号车马坑的坑底,陆续出土了6匹马骨架,令人不解的是,马骨交叉错位,布局极其凌乱。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卢连成心头,他想到了第二种情况:根据经验,凌乱的主因常常来自于盗墓。卢连成难以克制自己的担忧。 按照考古学常识,车马坑作为陪葬坑,其附近必然有重要的墓葬。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引起卢连成的注意,村民告诉他,这片梯田不适合种植庄稼,原因是这里的土壤土质很硬,与别处不同。职业的敏感让卢连成意识到这里大有文章。 考古钻探工作重新展开,他们用皮尺圈出老乡指认的硬实土壤的范围。很快,钻探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就在车马坑的背后,紧挨着塬背的地方,发现有墓土的遗迹。经过数月的挖掘,一座封闭了近3000年的西周古墓开始向世人掀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挖掘出的茹家庄1号墓墓室分为甲乙两个椁室,分别埋葬着两具尸体。 考古队员首先将焦点集中在乙椁室。但乙椁室的尸骨保存得非常不好,骨骼已腐朽成一些黄色的骨粉。根据大量随葬兵器的情况,可基本判断1号墓墓主应该是男性。 甲椁室位于1号墓墓室西部,体积略小于乙椁室。这里还残留了部分骨骼,可判定埋葬的是一位西周女子。 考古人员作出了初步判断,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倪姓女子 年轻的卢连成并没意识到,这个貌似普通的墓葬会带来众多未解谜团。 要揭开古墓的秘密,首先要从墓底出土的青铜器说起。 青铜器上的铭文是7个古怪的文字,起首的那个字应当是墓主人的姓氏,但它早已不在现代汉字的范畴之内。 卢连成说:“当时我们主要考虑到这个字的主体是鱼,旁边从弓从鱼,所以发鱼声。铭文里有鱼伯作器,或者鱼伯为其他贵族作器,所以我们基本就确定了茹家庄1号墓就是鱼伯自己的墓葬。”铭文上提及的鱼伯究竟是谁? 卢连成想起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挖掘车马坑时,马骨附近有一些奇怪的印痕,很像是苇席的纹理,这说明殉马入葬时被苇席包裹住,属于一种级别较高的入葬方式。 更为有力的证据出现在那个埋葬女性尸体的椁室里。就在这里出土了五鼎四簋的青铜礼器组合,在鼎和簋的口沿上铸造有文字“儿”,考古人员称之为“倪”。 这个倪姓女子显然是青铜礼器的主人。 卢连成他们当时推测墓主人身份大概应当是五鼎四簋一级的诸侯,把鱼伯基本上确定为西周畿内的一个异姓诸侯国的小国国君。 就在考古队为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时,接踵而至的清理工作却让他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道时,首先挖出了一块块支离破碎的骨头。这些骨头散乱在墓道中,最终拼凑出了一个人的形状。 接着,又在人骨附近发现了一些碳化物质,碳化物质还保留着最初的形状。这是一些被火焚烧后的竹节。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令考古学者想起早先发掘的1号车马坑:马骨交叉叠压、布局凌乱。 卢连成初步推断:茹家庄鱼国墓地在进行墓口封实前,曾举行过某种殉葬仪式,焚烧竹节,肢解奴隶作为人殉。 紧接着,他们在1号墓的二层台地上又发现了一个双手被缚的人体骨骼,这个人体骨骼扭曲着身姿,双手蜷伏胸前,仿佛在展现生前的痛苦。他可能就是一个殉奴。 被发掘出来的殉奴越来越多。1号墓中发现有奴隶骨架7具,两具在墓道口的填土中,5具在二层台上。人殉的出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将是一个重要证据,使卢连成对先前的推断产生了怀疑。 姬妾殉葬 考古专家对于1号墓墓主的夫妻身份产生了质疑,质疑源自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 卢连成发觉1号墓的主墓室内,甲乙椁室一大一小并排安置,口沿平齐,椁室上层的夯土层次清晰,没有任何搅乱和相互打破的现象,这意味着椁室是一次构筑的。很显然,这位倪姓女子与鱼伯应该是同一次下葬的。 在同一个时段,同一次下葬,那么必有一人是属于陪死殉葬的性质。 于是,两人的关系再次成为谜案。如果按照先前的推断,她是鱼伯的正妻,那么这种正妻殉葬的制度显得匪夷所思。 考古队员清理1号墓墓边时,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墓葬,他们将其称为2号墓。 经过测量,人们发现两座墓挨得非常紧密,以至于在挖掘2号墓时,侵占了1号墓的墓室边缘。2号墓墓室的一角打破了鱼伯墓的一侧,这个打破关系就证明两座墓有时代早晚的关系,2号墓主人要比1号墓主人晚一点去世。 2号墓是一座形制较大的墓葬,墓中共出土刻有铭文的青铜器10件,多数为鱼伯为井姬作器。众多青铜礼器表明井姬生前地位十分显耀。 卢连成说:“井是周公的后裔。井伯和井叔从西周中期就是王朝的执政大臣,辅佐周王和天子处理政事,是王朝非常显赫的贵族。井姬可能是他们其中的一代女儿嫁给鱼国国君,作为鱼国国君的夫人,也就是正妻。” 那么,1号墓中青铜器铭文所示的“儿”,其身份绝非正妻。卢连成判断,1号墓的倪姓墓主,基本能确定是为鱼伯殉葬的,是鱼伯的一个姬妾。 寻找家族墓葬 为寻找历代鱼伯的家族墓葬,考古队走遍了数十个西周遗址区,但历时数年的勘察工作未见任何成效,卢连成陷入了困境…… 若找不到历代鱼伯的家族墓葬,就无法证明鱼国真实存在。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扭转了卢连成的困境。 1976年10月5日,在距离茹家庄3公里外的竹园沟村,村民们在田间劳动时在黄土下发现了一个黑黝黝的洞口,里面有一些形状诡异的器物。考古队员闻讯后急匆匆地赶赴现场。 经过挖掘,一些青铜器露出了土面。青铜礼器的铭文表明墓主叫鱼季,鱼季墓年代大概在昭王时代,就是西周早期稍微偏晚一点。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又是一次偶然的发现使一处鱼国墓葬群进入考古队员的视野——宝鸡市区西部的纸坊头村。 纸坊头的鱼国墓地出土了一些器形较大的青铜器,其铭文自称为鱼伯、鱼伯作器、鱼伯自作用簋。从铭文的体例、器形、花纹,以及墓葬形制规范的情况看,它是迄今为止在宝鸡地区鱼国墓地中间最早的第一代国君。他的活动年代基本是文王晚期到武王,估计墓葬下葬的年代可能到成王的初年。 纸坊头鱼国墓地在渭水北岸,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庄重雄伟,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的景象。 竹园沟鱼国墓地则退至渭水南岸,活动年代大约在西周康昭时期。 茹家庄鱼伯墓地晚至穆王初年,这时已是全然衰败的景象,而且有逐渐往南方退让的趋势。 至此,已经基本理清鱼国国君的世系。 但这个非姬姓的小国从何处而来,他们在西周王畿之内生存了多久,有没有可能找到年代更晚的鱼国国君墓地呢? 亡国厄运 卢连成重新回到茹家庄墓地,再次考证墓室。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先前被忽略的迹象。 考古工作者发现在墓地二层台地上填埋着花岗岩砾石块,这些砾石块也有一些散放在墓主周围或铺垫在尸体下。石块多呈椭圆形,大小不等,未经加工,均采自清姜河。 卢连成说,这种砾石块应该是当时埋葬的一种习俗,但不是周人的葬俗。 考古队员将视线转向鱼国墓地出土的其他文物上,他们修补了林林总总的陶罐,试图从这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这些生活常用的钵形尖底罐,是一种地域特征极强的器物,很少见于典型的周人遗址和墓地,却多见于四川新繁、广汉早期蜀人遗址。这说明,鱼国墓地遗物呈现出早期巴蜀文化的某些特征。鱼国,这个史籍失传的古国,在考古中逐渐复原。 考古队在茹家庄又发掘出一个神秘的墓葬,令人惊奇万分的是墓室内并没有棺椁…… 在墓穴西北角有一个土台,台上有人骨架一具。尸体的骨骼保存非常好,是个壮年男性。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个骨骼颈部有皮条缠勒的痕迹,好像是一具被皮条勒死的尸体放在墓中的夯土之中。 考古人员试图找到一些随葬品,但是直挖到墓底,也没发现任何葬具和器物。 有专家认为,这是个奴隶,是被生殉的。 但卢连成对此论断颇为怀疑。 卢连成认为,这可能是亡国的鱼国国君,他在修筑墓葬时这个国家还存在,但墓葬修成了还没来得及举行隆重的下葬仪式,国家就出现某种变故,所以这个墓没按正常情况来使用。 古鱼国,这个西周王畿之内受到册封的非姬姓诸侯国,其国君为了在周人的京畿之地立足,试图通过婚姻外交以求附庸姬周的王室家族而生存,并且巩固地位,但还是败于错综复杂的宗族斗争,鱼国最终难以逃脱亡国的厄运。 最后一代国君屈死在空旷的墓室中,没有任何人陪葬。而鱼国的下层族人,很可能穿越秦岭,回到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