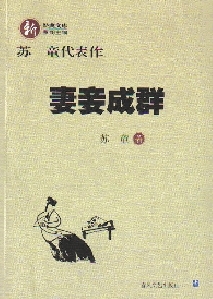|
 |
|
|
|
||
|
|||||||||
□晚报记者 陈泽来 实习生 陈晓雪 曹莹 电影和小说只是一种亲戚关系 记者:你的成名作应该算是1987年发表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而你为大多数人所知却是《妻妾成群》被改编成电影。后来你的《红粉》《妇女生活》和《米》也被搬上了银幕。你认为影视对于提升你名气的影响大吗?改编的电影是否符合你心目中人物的形象?你能否评述一下当前影视与文学的关系。 苏童:我一直认为,影视的传播对作家寻找潜在读者是最好的方式。我有一些读者,也是从影视那里跑来的。我的那些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幸运的是都落在好导演手上,基本上是满意的,但实际上我不满意也无济于事,电影是导演的,小说是我的,它们的关系可近可远,因为只是一种亲戚关系。 记者:你是否想过要从事影视剧的创作?你怎么看待目前的文学商业化倾向? 苏童:我一度尝试过影视剧创作,实在不喜欢那种“胸怀他人”的状态,只好半途而废了。商业化的文学,在任何国度都是一个普通的文学业态,与阅读市场需求相对应,并无贬义,看你要选择什么,选择市场还是选择你内心的那个梦想?当然,我们有很好的令人惊喜的例子,比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不是为市场写的,却在市场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记者:在你的小说中,往往对女性心理的体会准确而独到,并因此而吸引了大批女性文学粉丝,请问这与你从小所受的教育和成长于江南水乡有无必然的联系?如果有联系,又有着怎么样的联系? 苏童:以我的观察,小说的阅读人群中,本来就以女性居多,我不知道我的女性缘是否比别人好一点,也不知道这与我的生长环境是否有内在联系,我知道很多读者喜欢我的《妻妾成群》《红粉》那样的作品,但是对于我来说,不可能再回去“拾玉镯”了。 记者:你在小说中多次写到“绳子上悬挂的是春天”,如《米》中施云、琦云姐妹俩,《河岸》中的乔丽敏。女人都喜欢保存自己喜欢的衣服,这是否暗含着你对女性的某种看法和认知? 苏童:女人和衣服的关系真的是值得探究的,女人喜欢保存她心爱的衣物,通常缘于心爱的衣物上凝结着美好的记忆,她的内心大概是要保存那份记忆。在类似的表述上,我记得王安忆说过,女人的一大特点是,她们鉴别事物不太信任五官,更信任手的触觉,她说女人买东西都喜欢用手去摸一下商品。我想保存衣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要保存那份触觉吧。 记者:“写短篇是一种享受,而长篇不能按照个人兴趣来写,必须科学,非常累人。”《米》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用了半年的时间。而在《河岸》创作过程中,你三年三易其稿,从国外写到国内,从第三人称写到第一人称,如此的投入与认真,是什么促使你进行这部长篇写作的? 苏童:人到中年,对创作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不求效率,只求品质了。写《河岸》前后大约用了两年半时间,像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与其说灵感,不如说是一个愿望促成了这部小说。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河流关于船的小说,最重要的原因与我祖辈和我自己的成长有关。我祖辈生活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上,而我自己是在河边长大的,现在也住在长江边,我认为河流就是我的乡土,至少是乡土的重要部分,写河流就是写我的乡土。 《河岸》是我最好的小说 记者:你曾经说自己写《河岸》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为什么呢?对于写作,你认为作家写作的第一出发点,永远是完善自己的生活,表达心灵世界的东西。通过《河岸》你想表达什么? 苏童:一个人在用文字折磨自己那么长时间后,一旦解脱出来,其实都有新生感的。这部小说如果要用一个很切题的名字,应该叫“河与岸以及船的故事”,但是我想还是叫“河岸”更加自然一些。 在小说中,我无意用河与岸或者船去象征什么,但我确实想试图通过这三足鼎立的事物建立一个维度,去观察人的处境。船与河是一组关键词,房屋与岸是另一组关键词,其实船上生活无关放逐,也无关苦难,河与岸不是世界的两极,船在河上走,人在岸上住,河流与岸都可成为人的乡土和家园,只不过它们戏剧化地成为一组参照物。在《河岸》中我努力探索这组参照物的奥秘,因此,《河岸》乍看沉重而悲伤,其实是探索生存之奥秘,背后有一种乐观主义在支撑。 从故事层面上解读,这就是一个关于“寻找”的小说。《河岸》的主要人物是三个孤儿,我说的寻找主要建立在这个意义上,是三个孤儿的寻找,这几个人物都被命运放逐或者遗弃走到一起去了,他们与河水有纠葛,与岸有纠葛,他们之间也有密集的纠葛,他们注定有不幸,而他们各自的生活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寻找,孤儿们该寻找什么呢?我想他们首先要寻找母亲,这是一个共同点;其次寻找身份,寻找家和乡土,寻找爱,或者干脆说,他们必须寻找天堂。 记者:王干评价说,在《河岸》中可以读到莫言对历史的迷惘、马原的叙述圈套、余华的暴力恐怖话语、格非的象征谜团、孙甘露的语言雾障、叶兆言的家族沧桑、北村的灵肉冲突、陈染和林白成长的青春苦闷,甚至还有安妮宝贝式的忧伤。你认为在《河岸》创作过程中,自己有哪些方面的突破?与以往长篇的创作有什么不同?“超越自我”这个评价你认为符合不符合你的状态?是否太重了? 苏童:“超越自我”是一句被说滥了的人生格言,但我一直很喜欢这四个字的意义。我并非在《河岸》中第一次做所谓“超越”的动作,但在《河岸》中,我第一次面对一个宽阔而严峻的小说空间,要求自己以最精确的姿态潜伏进去,这似乎有难度,需要耐心,也需要勇气。我自认为潜伏成功了。 记者:你说《河岸》是你最好的小说,这和现在很多作家常常宣称自己的“下一部”才是最好的一部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如此坦白直率,实在很让人敬重与赞赏。但是有些人评论说,你说这句话为时尚早,你的观点是什么? 苏童:我说这话时是真诚的。但是,所有的宣言都不一定可靠,何况是一个作家出版新书时的宣言,你是有理由保持警惕和质疑的。我的观点是面对一部新作,它本身是一种风险阅读,有可能别人的喜悦是你的沮丧,也有可能别人眼里的缺陷是你眼里的美好。所以,读者应该撇开作者和评论都说了些什么,自己去评判。 记者:你在接受新浪读书网采访时说,在《河岸》中你还是有一些遗憾的,对于故事节奏你并不是很满意。你能透露下你所说的遗憾是哪些吗?该书再版时你会考虑重新修改吗? 苏童:《河岸》成稿时废弃了六七万字,都是因为沉溺局部而对小说整体构成了累赘。这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河岸》起初是用第三人称。第三人称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叙述方向上,线索多了,故事显得太紧张太局促,而且文字有点乱。后来改成第一人称,觉得整个叙述松弛多了,也自然多了,但小说的节奏还是有点前慢后紧。既然已经出版了,就留着那些遗憾吧。我不喜欢作修订版,无穷尽的修改不一定带来完美,我情愿完美是一个梦想。 作家不是专门向人生献花的 记者:有人戏称你为中国最黑暗的小说家,你如何看待这种黑暗?你平时关注评论界对你的评论吗?一些不恰切的评论,是否会左右你的创作态度? 苏童:我不知道“最黑暗”的封号从何而来,也许是在暗指我作品中的世界缺乏亮色和温暖。其实我觉得作家这个角色不是专门向人生献花的,更多的时候,倒是与外科医生有相似之处,喜欢手术刀,就对细菌、疾病和病变敏感一些,手术温度很讲究,冷一点比热一点好,我对外界的评论是留意的,它对我的诱惑有点像社区宣传栏的留言,很好奇,看一看,但它不能改变我的创作态度。 记者:《已婚男人》《离婚指南》这两部小说都表现了已婚男人由对婚姻的理想到对婚姻的绝望。有意思的是,里面的男人都对哲学情有独钟,每遇困境,屡屡用哲学来安慰自己。这是否间接表达了你认为哲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看法?你对哲学持什么态度? 苏童:哲学从来不是解决面包和婚姻问题的,更无法提供对付人生困境的良方,所有的哲学思想都建立在人类迷惘的需求上,人类迷惘是正常的,哲学给你提供思考和求解的方法而已。 记者:你小说中描写的孩子大都缺乏性知识,父母对于性知识也都耻于向孩子开口,你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过性启蒙教育吗? 苏童:我女儿的性启蒙教育由我太太负责。时代不同了,性愚昧是我们那个时代青少年的特征之一,现在不是了,现在要担心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记者:小说《米》中我们读到了你对故乡的依恋,还有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亘古情怀,这部长篇处女作对你后来的创作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苏童:是一个开始。《米》是对人性世界一次“癫狂”的探索,是我的文学“青春期”的产物,我很珍惜。但是正如《米》本身的“破坏性”,我不仅愿意破坏别人的作品,更愿意破坏自己的,所以,《米》最终也被我背叛了。 记者:多年来,你糅合写实手法和现代技巧创作了多部历史小说,请问你自小就喜欢历史吗?你在小说中又是怎么处理真实的历史和有机的虚构之间的关系的? 苏童:除了《武则天》,我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其实是门外汉。我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是虚构的产物,而虚构本身是与记忆不可分割的,渺小的个人记忆中从来都躲藏着历史这个巨人。说到《河岸》的创作,我从小临河而居,见过无数的内河船队来来往往,但小说中的向阳船队有点特别,这是一支“赎罪”的船队,我其实没见过这样的船队,但我小时候见过无数赎罪的“罪人”,我把他们编到一支船队里去了。 记者:最后想问一下,从注重语言的形式到注重小说的内容,你认为在《河岸》中自己是否做到了? 苏童:小说是语言和内容的有机体,没有一部好小说是用不好的语言完成的。《河岸》的写作过程中,我只是努力地寻求最合适的语言去完成我的叙事目标,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