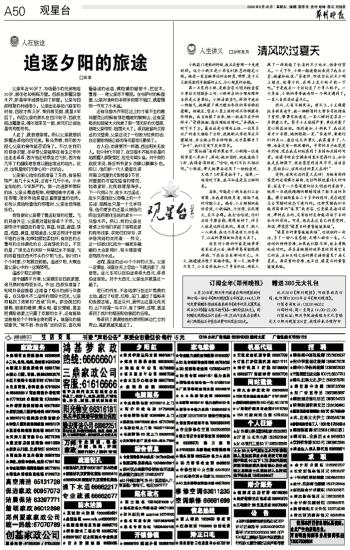|
 |
|
| 3上一篇 下一篇4 |
|
|
|
||||
|
□庄学 父亲年近90岁了,与他最小的兄弟相差20岁,居住处却相隔万里。四叔在新疆乌鲁木齐,那是早年间漂泊到了那里。父亲与四叔相聚的时间很少。父亲出去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四叔才两三岁,等到再见面,就是8年后了。而后父亲的部队在四川驻守,四叔支援边疆建设,偶尔回来见一面,弟兄们之间也是匆匆复匆匆。 人老了,就极想亲情。所以父亲就想到新疆去看他的四兄弟。鞍马劳顿,我们极为担心父亲的身体能否受得了。不过,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却希望父亲能够在有生之年外出走走看看,因为他还没乘坐过飞机,因为有几年了的腿疾难愈难以跑出很远的地方。此次,也算是我们尽孝心的一次机会。 父亲细心地给四叔准备了东西,有洛阳特产,有几十头大蒜,还有十几斤小米。小米金灿灿的,今年新产的。第一次进新郑国际机场,父亲头戴遮阳帽,府绸短袖中式褂,手拄拐棍,很华侨地看着这富丽堂皇的处所。安检认真地检查他的拐棍时,父亲也觉得挺乐的。 我特意给父亲要了靠近舷窗的位置。飞机昂首升空,父亲就对着舷窗看个不停。父亲惊讶于蔚蓝色的碧空,深蓝、淡蓝、蔚蓝、绿蓝、浅蓝、黄蓝,层层递进;父亲还惊讶于延绵不绝的云海,如棉如絮如柔如纤,有灰色的云雪样的云淡黄色的云,还有绿色的云。不变的是,广垠无边的天际一抹橘红永不消退,飞机向着挂在西天尽头的夕阳飞去。航行的4个小时里,夕阳就在前面。追逐夕阳,大概也是父亲心中的一丝期望吧。 追逐夕阳之旅哦! 由于腿脚不方便,父亲就住在四叔家里,弟兄俩时有彻夜长谈。外出,四叔给准备了轮椅并亲自推着,还准备了喝水的旅行保温壶。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国际大巴扎,父亲领略到了浓郁的“西域”风味。那些微凹的眼睛,细细的峨眉,戴头帕,着长绸裙,甚至把满脸都蒙上只露了双眼的女子,还有挺鼻梁曲卷发个个帅得出奇的男子。城堡似的高塔建筑,“阿不都·热合曼”类的店名,喜欢用叠音词的话语,满柜铺的葡萄干、巴旦木、雪莲……使父亲目不暇接。在哈萨村的帐篷里,父亲对美味的手抓羊肉赞不绝口,就着馕饼一气吃了小半盆。 还有乌鲁木齐市区边上的寸草不生的雅玛里克山和鲜有绿色植被的蜘蛛山,还有呈褐色如同被大火烧焦了般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都使父亲惊叹:祖国太大了。看到寂寥而又深远的戈壁滩,父亲还说了一句极为经典的话:在这里修铁路公路可得可着劲儿勤修了。 古人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如今时代不同了,在乌鲁木齐有许多是内地援疆人群聚集区,处处可闻乡音。对于我的叔叔来说,每日听听家乡戏聊以解解乡愁。所以,他们那一代人最喜欢看河南卫视里的《梨园春》节目,对里面的守擂攻擂者的情况,如数家珍,比我都清楚得多。下一代则认为,故乡太过遥远,故乡只是挂在父母嘴上的一个名词,祖籍也只是一个文字符号,他们更多的还是认同他们所出生所居住生活的家乡——乌鲁木齐。所以,我的父亲在餐桌上给他们讲起了洛阳老家的陈年往事,讲我们的爷爷,讲伊洛河间的夹河滩……终究,这一切都幻化成为一幅其乐融融的大合影照片,将乡情亲情定格成为永远。 返程,是坐的近40个小时的火车。父亲一定要坐,说是在天上忽地一下就到家了,没意思。坐火车可以在沿途看看大西北,看看沿途景致。对于大西北,父亲也许就是这一趟了。 夜行的列车,不舍地穿行在这片荒漠的土地,越过了哈密、红柳、玉门,越过了嘉峪关和张掖古城。接近兰州,虽然山还是光秃秃的,山下却是一马平川,有了绿树、庄稼,甚至看到了成片的稻田和收割后的谷堆。 等看到了黄黄浊浊的渭河和岸边伫立的青山,离家就越来越近了。 |
| 3上一篇 下一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