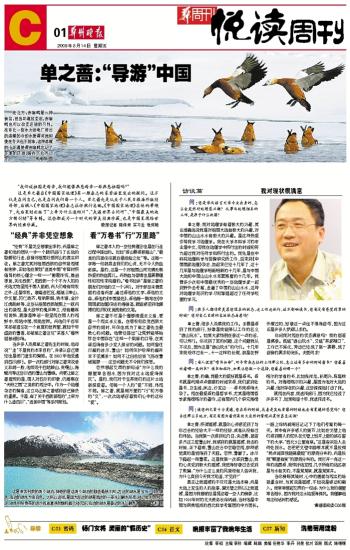|
 |
|
|
|
||
|
||||||
在北方,赤麻鸭是一种候鸟,但当环境改变后,赤麻鸭也可以改变迁徙的习性。在东北一些水力发电厂排出的温暖的冷却水使得河流即使在冬天也不封冻,这种温暖的小环境使得赤麻鸭忘记了冬季的迁徙,留在了北方过冬。周海翔 图 “我们说祖国是母亲,我们能像熟悉母亲一样熟悉祖国吗?” 这是单之蔷在《中国国家地理》某一期杂志的卷首语里发出的疑问。这不仅是在问自己,也是在问我们每一个人。单之蔷先是从业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部,后调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任执行总编。《中国国家地理》在他的带领下,先后策划出版了“上帝为什么造四川”、“走遍世界去问河”、“中国最美的地方排行榜”等专辑。这些都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经典珍藏,也是中国呈现给世界的经典珍藏。晚报记者 陈泽来 实习生 张何艳 “经典”并非凭空想象 “经典”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单之蔷和他的团队一步一个脚印进行了实地的勘测和行走,自身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真实印证。单之蔷尤其对祖国西部的自然景观情有独钟,正如他在策划“选美中国”专辑时所倡导的核心理念一样——“颠覆传统,推进审美,关注西部”,把西部一个个不为人知的天地尤物呈现于国人面前,而人们唯有惊叹之外,还是惊叹。像南迦巴瓦、稻城三神山、乔戈里、冈仁波齐、喀纳斯湖、纳木错、金沙江虎跳峡等,这些从祖国西部版图上一跃而出的景观,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没有雕琢和装饰,就像是神话一般呈现在国人的视野中,惊艳中国、惊艳世界。而他们千百年来却被遗忘在一个寂寞的世界里,就如千年盛放的雪莲,却被单之蔷这位“采莲人”蓦然回首间拾得。 当许多人羡慕单之蔷先生的时候,他却说“‘走’不是我的本来目的”,并承认自己曾经也是闭门造车的编辑。在2003年他受邀到四川旅行。那一次的旅行对单之蔷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他惊羡于四姑娘山、贡嘎山、海螺沟等这些川西的雪山与雪峰。而更让单之蔷震惊的是,国人对四川的印象,仍局限在“天府之国”之美称的观念中。作为一个地理杂志的编者,这立马让单之蔷感到自己身负的重责。于是,有了关于西部景观的“上帝为什么造四川”、“选美中国”等系列策划。 看“万卷书”行“万里路” 单之蔷本人的一些经典理念也是在行走过程中提出的。比如“看山要看极高山”,“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危险之处”等。这每一字每一句都直击我们的心灵,无不令人热血澎湃。是的,这是一个对祖国山河充满无限热爱的热血男儿。而热血与豪情也是需要理性和知性来构建的。“嗜书如命”是单之蔷的朋友们对他的又一个评价。对于那些未曾素面的读者而言,通过看他的文字、看他的文章、看他的《中国景色》、看他每一期写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卷首语,就能感受到他渊博的知识和优美流畅的文笔。 单之蔷不仅是个理想浪漫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赞叹和欣赏西部大自然的同时,环保也成为了单之蔷先生最揪心的问题。他曾经提出“让荒野能够始终在中国存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口号,在其背后得有多少发人深省的问题。如何留住川藏的冰川、雪山?如何保护珍稀的藏羚羊不受捕杀?如何不让白色垃圾飞扬在雪域高原……这些问题无不令我们深思。 忽然想起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的,我们对于生养我们的这片土地都深爱着。但每一个人的“爱”不同,体现不同。单之蔷,就是用万里的“行”和万卷的“文”,一次次地感召着我们心中的这份“爱”。 访谈篇 问:您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怎么会突然对地理感兴趣?从事与地理相关的工作,是源于什么机缘? 单之蔷:我对地理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其实准确地说我是对祖国大地有极大的兴趣,对中国的山山水水有极大的兴趣。是这种热爱引导我学习地理学。我在大学本科学习的专业是中文,但我在地理学中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超过我对任何学科所付出的。我先是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工作,后来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加起来已经十几年了,这十几年是与地理学相砥相砺的十几年,是与中国大地和中国山山水水耳鬓厮磨的十几年。我曾多少次和中国最优秀的一些地理学家一起到野外去考察,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这种对地理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超过了任何学校里的学习。 问: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您现在的状态,边工作边旅行,还不影响读书,您有没有感觉到累的时候?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单之蔷:很多人羡慕我的工作。主要是看到了我的旅行,好像是我能够以工作的名义“游山玩水”。如果大家特别在意这一点的话,可以转行。你谈到了累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从不谈及,因为这是“游山玩水”的代价。十几年来我没休过五一、十一这样的长假,都是在野外度过的,好像这一点也不值得自夸,因为这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你问我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我的回答是满意。既能“游山玩水”,又能“养家糊口”,工作已不异化,劳动已经成了第一需要,成了自身的需求和快乐。夫复何求? 问:有人说您“嗜书如命”,可平常杂志社的工作那么忙,怎么还有多余的时间看书?您最喜欢看哪一类的书?读书和旅行,如果让您做一个选择,您最喜欢哪一个? 单之蔷:的确,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看书就是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来看,我们家到处是书,卫生间、床边、沙发边……看书我看得太杂了。现在最爱看的是哲学书,尤其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作,还有国内几个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的书,比如张祥龙、孙周兴、陈嘉映的书。对海德格尔的兴趣,是因为他对大地的兴趣,他对存在的兴趣,这些深深地打动了我。 就现在而言,我选择旅行,因为我已经读了许多书了,如果倒退十年,我选择读书。 问:读您的文章十分震撼,您在写的时候,或者是实地考察的时候也会有震撼的感觉吗?您去过那么多地方,有没有因为看到某处大自然的景观而震惊甚至流泪? 单之蔷:所谓震撼,就是你心灵感受到了与你过去的经验大不一样的经验,或者从没有过的体验。当我第一次看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杰这三座雪山时,我感到的就是震撼,我去的时候,正下着雨,雪山在云中忽隐忽现,那种感觉真的是觉得到了天庭。忽然,雪崩了。冰川下腾起一阵雪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山,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我觉得好像过去受到了欺骗:“为什么这么美的风景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才见到?” 真正让我震撼的不仅仅是大地本身,而是大地上发生的人的故事,黑戈壁之所以让我震撼,是因为我眼前总是晃动着一些人的身影,比如1926年时的北大教务长徐炳昶,当时他是中国与瑞典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一路上徐炳昶用日记记下了他们考察的每一天。其中有许多感人的细节,比如在戈壁上他们看到商人的驼队在戈壁上划开上面的砾石留下的大字:“西北5公里有泉。”这是告诉后人去何处找水。在茫茫戈壁中路根本就不是按照“两点间直线距离最短”的原则分布的,而是按照“哪里有泉”的原则分布的。我打开一张这一带的地图看,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地名都是与水有关的,不是某某泉,就是某某井。 当你身临其境时,心中的画面与现实的场景重合时,与其说是震撼,不如说是感动和融入。我常常想起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理解他写这句话时的感受。 请继续阅读C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