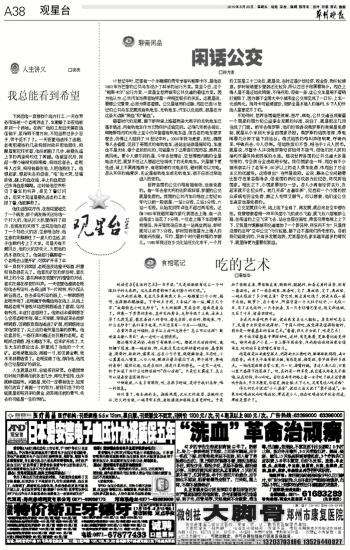□孙方友
17世纪中叶,巴黎有一个半瘫痪的青年学者叫帕斯卡尔,是他在1662年为巴黎的公共马车设计了科学的运行方案。直至今日,这个“帕斯卡尔”运行方案,一直是全世界城市公共交通的最佳方案。因为他认为,公共汽车与乘客始终是一种相互吸引的关系。这就是说,要想公交繁荣,必须为乘客着想。公交是城市的动脉,现在已由16世纪的公共马车发展成有轨电车、无轨电车、汽车以及地铁,都是在为这条大动脉“换血”和“输血”。
随着时代的发展,眼下那种背上拖着两条大辫子的无轨电车已基本绝迹,而有轨电车作为文物保护还能见到。记得几年前去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至今仍保留着有轨电车道,很古老的电车驶来驶去,仿佛让人回到了18世纪中叶。2006年我与麦家、王松、魏微等人去香港,见到了英国式的有轨电车,进站出站都是摇铃铛,车速也不是太快,像个老奶奶似的,可能是为了让乘客们观市容,颇具古典风味。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今年去世博会,见世博园内跑的全是电动大巴,就禁不住让人想起已经消失了的无轨电车。只是眼下更先进,背上不需再拖辫子,有很简便的充电系统,随时就可以充电。若从环保的角度讲,无论是有轨电车或无轨电车,都不应该过早地进入历史的。
世界各国的公交价格有高有低,也有免费的。有一年去意大利的比萨看斜塔,那里的公交就是免费的。我国的公共汽车价格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般都是:一站2分钱,三站5分钱,六站一毛钱。从始发到终点也不超过两毛钱。记得1980年我随河南作家代表团去上海,有一次逛街坐3站花了5分钱,一位老上海下车后便笑我傻鸟,并开导我说应该走一站再坐两站,那样就可以省下3分钱。那时刻我很是为上海人的精细而叹服。节约,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字眼儿。1980年我还在乡文化站任文化专干,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二块五,就是说,当时还是计划经济,钱金贵,物价较便宜。那时候城里乡里都还比较穷,所以过日子很需要算计。现在上海人是不是还如此精细,不得而知,但有一条,坐公交车是用不着精打细算了,因为眼下全国大中小城市坐公交早变成了一口价:上车一元或两元。持月卡可能便宜些,但那全是本城人的福利,乡下人和外地人是享受不了的。
不知何时,世界各国竟把教育、医疗、邮电、公共交通当成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和公益事业发展的标准,说白了,就是把这几项当成了门面。前年去俄罗斯,他们的导游说俄罗斯的教育是免费制,就是从小学到大学全由国家负担。俄罗斯的地铁很深,乘电梯要几分钟才能下到站台。俄式地铁的鸣叫声很响亮,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令人恐怖。但地铁票价不贵,相当于2元人民币。就是说,尽管外人评说俄罗斯经济如何不景气,但他们对人民的福利尽量保持前苏联的水准。据说世界各国的公共交通大多是亏损的,亏空部分全由政府补贴。我们国家也一样,现在有不少城市都实行了老年卡,60岁以上的老人乘车免费,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钱谁出?当然是政府。论说,解决公交问题要比医疗改革容易得多,但美国的两位总统都为此犯愁,何况其他国家。相比之下,小国家要好办一些。若人少再有经济实力,办起来就不会犯头疼。前几天看“走遍亚洲”,见西亚一个小国的民众看病吃药全免费,颇让人吃惊又眼气。可以想象,他们坐公交车肯定也是免费的。
公交发展到今天,地上地下全有了,再发展,就应该在空中想办法。我曾想象着用一种环保型小飞机或小飞船,就飞五六层楼那么高,在街道的上空飞来飞去,站台也搭在高处,乘客可乘电梯上上下下,又算是为缓解城市交通增加了一个新品种,何乐而不为?只是我设想的这种“空中公交”代价较高,眼下还不是我们所考虑的。目前我们能做到的,只有多发展地铁,尤其是在私家车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