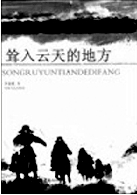|
 |
|
| 3上一篇 |
|
|
|
||||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赵东明再也没有起来 胡伟强打眼一看,那条鱼有一两多重。急忙说:“快放了。这冰河的鱼没三几年时间长不到那么重,放了,放了。”“你看胡伟强,天上地下没有不知道的。”刘大刚对郭双喜说。“人家是西安郊区长大的。”郭双喜道,“见识多,又上过高中,要不,孙副指导员咋叫他机灵鬼呢。” 两个班长一个生在甘肃,一个籍贯河南。在三连,这两个省的兵加起来就有40多人,没事儿时总往一起凑。他俩也不例外,闲暇时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看,你看看,何玉一个裤头洗了恁长时间,肯定是‘跑马’了。”郭双喜嘻嘻笑着。 刘大刚只是抬眼看了看,何玉毕竟是他班里的战士。何玉确实是“跑马”了。他手上洗着裤头,嘴里念念有词。“孩儿啊孩儿啊慢些走,可别碰上大石头,不是你爹心肠狠,没娘的孩子难收留……” 在常青谷,有人喜欢热闹,也有人喜欢安静。九班班长杨留旺就一个人坐在坡顶。他两眼扫过河流,扫过红柳,扫过绿草茵茵的河坡,定定地注视着第四座烈士墓下长眠的赵东明。1968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奇寒无比的夜晚,赵东明在瞭望哨上连着站了两班岗,第二天就高烧不退患了肺水肿。多站的一班岗,正是为杨留旺站的。杨留旺永远都会记得12月19日那个下雪的日子,正是这一天,他感冒了。巴托哨卡有个规定,凡是感冒患病的战士,一律不站营区哨和瞭望哨。杨留旺从连部卫生室拿了药,卫生员要向连里干部报告,他坚决阻止,说:“俺是才当兵几个月的新兵蛋子,就这点小感冒,又不发烧,不就是站一个小时哨吗,千万不要跟连里领导报告。”“这是连里规定……”杨留旺打断卫生员的话,说:“咱俩可是老乡,这点忙还不帮。”瞒过了连干部,但和杨留旺铺挨铺的赵东明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临睡前他问:“你几点钟站哨?”“夜里12点。”杨留旺知道,赵东明站完岗就轮到自己了,便提醒说:“你早点给值班室打电话,让值班员叫我。”“放心睡吧。”说着,赵东明钻进了被窝。 起床号叫醒了杨留旺。他起身一看,赵东明躺在旁边的被子里。“起床了,快起床出操了!”班长喊着。 赵东明再也没有起来,他被送到连部卫生室,一量体温39℃多,到了下午,赵东明病情明显加重,体温高达40℃,呼吸困难,胸闷气塞,一咳嗽就吐带白色泡沫状的痰。 “坏了。”连部医生余秀山对卫生员说,“典型的高原肺水肿症状,准备吸氧挂吊瓶。” 吊针一连打了三天,赵东明的脸由紫变青又变成灰白,咳出的痰成了粉红色泡沫。杨留旺一有空闲就来到卫生室,焦急地询问:“他病情咋样了?”“要是有高压氧舱就好了。”余秀山冒出这么一句。杨留旺听不懂,卫生员一脸无奈、一脸茫然。 第五天夜里,赵东明19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杨留旺号啕大哭起来。那一夜,赵东明没有让值班员叫醒杨留旺,他接连站了两班岗。瞭望哨设在营房后的山顶上,虽然四面玻璃门、玻璃窗密闭,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天气,山顶上风力更大,气温更低。戴上皮帽子、穿上皮大衣、蹬上羊毛毡筒,“全副武装”站上一小时,人就像掉进冰窖里。更何况,上下瞭望哨都要顶风冒雪走20分钟的山路。瞭望哨一冻,钢针样刺人的寒风一刮,赵东明浑身打起了哆嗦。 暑来寒往,一晃三年半过去了。杨留旺成了即将服役四年的老战士。今年该复员了?他产生了退役的念头,21岁当兵至今已经25岁了。在湖北的一个山村里,父母、弟弟还有妻子在等着他。前几天团长带来的11封信,有8封都是弟弟写的。信中说妻子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不和睦,从怄气升级为吵架,回娘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他担心啊,担心老人,担心妻子,担心整个家。 可是,他又不愿离开巴托哨卡。他有一个心结,总认为赵东明是为他死的。他总爱回想那个挥之不去的日子,他感冒了,还有点轻微咳嗽,那么冷的天站一个小时的岗,来回又得走40分钟,得肺水肿的可能就是他。还有那个卫生员,为这事受了处分,第二年就让他复员了。离开哨卡的前一天晚上,卫生员找到他抱头痛哭。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你说,我不多干几年能离开哨卡吗?!”他扪心自问,下定了坚守哨卡的决心。 不知什么时间,马前进也来到了常青谷,他和这个打过招呼,又和那个唠上几句,虽说来三连只短短四天,全连一百多号人的姓名、相貌已印在他的脑海里。“指导员,找人啦?”胡伟强走过来问。 李福根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8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