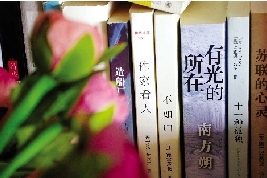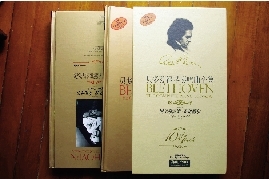|
|||||||||||||||
田艺苗 青年学者,音乐作家,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曾获国家文化部文华奖优秀音乐作品奖;出版著作有《流影流声》、《时间与静默的歌》、《温柔的战曲》、《靠谱》等。 田艺苗有两个书房。一个在上海城西,位置比较偏,但用她的话说是“比较有范”,那边有整面墙的CD,茶几是个巨大的鼓;还有一个在淮海路上,十里洋场正中心,特点就是书多、乱,但位置方便,她平时主要待在这里。 因为贪恋书多,我们最终还是放弃“有范”,去了她淮海路的书房。还没进门,隐约只见到客厅,就感觉我们来对地方了:无论是鞋柜、茶几还是餐桌上,严严实实都堆满了书。于是我们在群书中落座。在女主人泡茶间隙,环顾四周,除了书,就是乐器,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甚至还有一把尤克里里,像是刚被弹奏过,放在《读库》新出的《〈耕织图〉流变》上。“这里平时也会做些小型沙龙,主题无外乎音乐、文学、电影。这里的书也主要是音乐和文学占绝大多数,所以它算得上是个非常文艺青年的书房了。”端着红茶,田艺苗笑着说。 主要读国外翻译作品 莱昂纳多主演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田艺苗还没来得及看,但早按捺不住兴奋,因为她非常喜欢菲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我觉得他把握的状态非常好。对这个浮华社会,他既享受其中,又游离于外,明白这种生活其实极易幻灭。这种状态非常真实,不拜金,不愤世嫉俗,也不装,这样的适度其实很难把握。他的好作品很多,但奇怪的是,好像就《了不起的盖茨比》最风靡。” 说到这里,田艺苗放下茶杯,把我们引到了卧室,这里还有三个大书柜。靠阳台的地方,有一条小沙发,旁边胡乱堆着一沓书,这些都是田艺苗常读的书。最上一层放着的就是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除此之外,菲茨杰拉德的散文集,她也非常喜欢。 在这一堆书里,我们还发现了迈克尔·翁达杰的新书《猫桌》,再往下翻,又找到了《一轮月亮与六颗星星》,还有《菩萨凝视的岛屿》和《英国病人》。 “翁达杰的书,我也是见到必买,我从高中刚毕业就开始看他的书,他以写诗的方式来写小说,或者说他不是在写小说,他写诗,写电影,写音乐,写光影,而且他设计的场景非常有力。”田艺苗注意到了翁达杰晚年的转变,“他老了以后,一直在有意颠覆之前自己的套路,他变得更加繁琐,但也更加自然,你会觉得他的深情越来越多。” “我读的文学作品,主要还是国外的翻译作品,国内的读得比较少,除了上海本地的作家,比如说王安忆、陈丹燕,再有就是我一些朋友的作品,其他读得不多。”田艺苗总结道,这同她学习西方音乐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最重要的阅读。 所以在田艺苗的书架上,除了翁达杰、毛姆这些跨越东西方文明的作家外,很多书的出现,都是为了帮助她更加全面地去理解音乐。比如说弗雷德里克的《伪雅史》、勒佩尼斯的《何谓西方知识分子》,姜守明的《世界尽头的发现: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水手》,甚至是《汉宝德亚洲建筑散步》。 在田艺苗看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书都能成为她理解音乐的一个重要切口,“比如说巴赫,你只有在了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才能真正理解他的音乐,时代对于音乐风格影响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所以她很喜欢读艺术家的传记。“我喜欢埃克托尔·柏辽兹的回忆录,特别奔放,具有浪漫主义时代的气息,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想法。”除此之外,像《皮娜·鲍什》、坂本龙一的自传《音乐使人自由》,以及安迪·沃霍尔的自传都让她兴趣盎然,“真正个性鲜明的艺术家,给你的冲击非常大,他们能够改变你、塑造你。” “但传记要写好,并非易事。”田艺苗说。好的传记,像莫扎特的《Amadeus》,让人读完之后能特别理解这个人,也能再次理解他的音乐。但她最近读的一本披头士的传记,太把披头士写成故事了,却忽视他们作为时代代表的意义,让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其实非常难 田艺苗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作曲系的背景,难免让人想起刘索拉在《你别无选择》中的描述,但田艺苗笑着说,自己当年倒没有遇到这么些传奇的故事。 不过她很喜欢读一些音乐家写的书倒是真的,比如说保罗·鲍尔斯的《情陷撒哈拉》、科恩的《美丽失败者》。他们的著作中,有一种类似于音乐的迷人韵律感,让人读起来非常享受。 田艺苗自己也写作。同音乐学院许多老师把课外时间用来学生不同,她把更多的时间放到古典音乐评论和普及上。但在中国做乐评并非易事。“其实现在中国的乐评不是特别专业,真正的乐评应该是现场乐评,但如果你真写出来,能看懂的人很少。所以现在我的工作主要还是向大众推广古典音乐,让更多的人形成听古典音乐的习惯。” 田艺苗非常羡慕古典音乐评论家诺曼·莱布雷希特。她觉得莱布雷希特真正掌握了音乐和传播之间的平衡,在音乐上,他既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同时又了解大众的关注焦点所在,能把乐评做得具有社会学意义。田艺苗清楚,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尤其在中国,你可能会面临很多音乐之外的问题。不过她也认为,如果真正将音乐完全变成自己的生活,能从早到晚听,那就已经非常幸福了。 “我接下来可能不会全部写古典音乐评论,会涉及自己感兴趣的舞蹈、文学、现代电子音乐。”田艺苗希望自己能听更多的东西,在不同的音乐中最终听见的都是自己。“更关键的,是在聆听过程中,找到自己真正想听的东西。在这样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其实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当我真正明白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有切肤之痛之后,我可能就会找到自己在教书、写书评之间的平衡,或者说某种节奏了。”田艺苗觉得自己正慢慢朝这个目标靠近。 这可能也是所有与艺术有关行当的共性。“我最近看了杉本博司的《直到长出青苔》,他的风格那么纯粹,一定经过了一个艰难的尝试和精挑细选的过程。”田艺苗说,艺术的东西,如果你只是轻描淡写,肯定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道,才能真正震撼人心。 颜亮 南都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