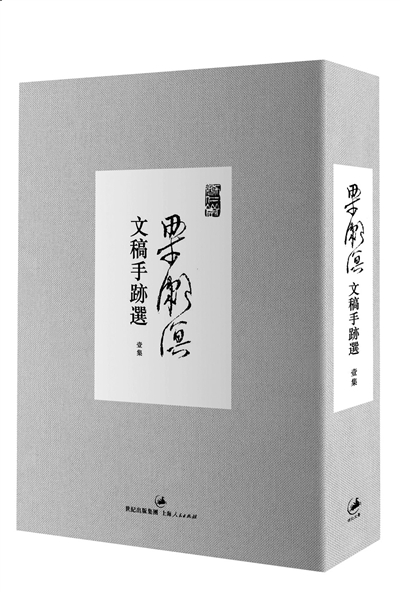|
|||||||||
“在台湾,大家认为梁漱溟留在大陆是附共,所以不能研究;在大陆呢,认为这个人是反共。国外没有这个框框。” 1969年至1971年,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艾恺想到大陆来。但时值“文革”,他只好转去台湾和香港,一边学汉语,一边寻找梁漱溟的学生、朋友,想通过他们更多地了解梁漱溟。“他们那边消息也不怎么灵通。譬如香港,他最忠实的一位学生胡应汉,也不知道梁在‘文革’时候的经历。牟宗三、唐君毅也没听说梁先生的消息。” 在台湾,艾恺采访了不下30个人,包括陈立夫、周绍贤(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等。但困难重重,“除了梁的一些书、著作之外没有别的资料,第二个困难当然是语言,我中文水平还是不那么高。比如(采访)钱穆,他的口音是最重的,幸亏我的一个同学是他的外甥侄,给我做翻译,把他的话翻成比较标准的普通话”。1975年,艾恺完成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书中的参考书目达611条。 台湾行让艾恺大开眼界,这才开始真正了解中国人。“我发现中国人的宇宙观跟西方不一样,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一个实体,不是单独的存在,一定是跟别的实体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刚到台北,我总得在街上问人某一个地方在哪里,在西方的习惯是说哪一条街多少号,中国人会告诉你,你要找的地方和别的地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某一个地方的北边,或某一个地方的后边。西方人是用二元论的逻辑,中国人,依我看,那是跟《易经》有关的宇宙观。”艾恺说,越了解中国,越觉得很有意思,越有味儿。从个人的性格和文化旨趣上,他尊崇中国儒家文化,他到山东曲阜孔庙会行礼,到梁漱溟先生的墓前会三跪九叩。后来,他不仅写下了有关梁漱溟的书,也写了《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著作。 台湾之行几年后,1979年,邓小平应卡特总统邀请访美,中美正式建交。艾恺也获得了到达中国大陆的机会,他以翻译身份到中国考察,并在1980年终于见到了梁漱溟。 为了见面,艾恺已经做了多次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两国开始了文化交流,艾恺作为中方访美代表团的翻译提出要见梁漱溟的请求,但没有收到回复。后来他才知道,1966年挨斗以后,梁漱溟原来住的房子被占了,只能与太太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没有书桌,也不许他见客人。 《最后的儒家》在1979年出版后,引起西方学界对梁漱溟的兴趣,并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在艾恺先生写这本书之前,还没有人写过我父亲的传记。在台湾,大家认为梁漱溟留在大陆是附共,依附于共产党,所以不能研究;在大陆呢,认为这个人是反共。在这种情况下,国外没有这个框框,所以有人研究,这人就是艾恺。”梁漱溟之子梁培宽、梁培恕接受纪录片《泊客中国》采访时说。对此,艾恺向记者举了个例子,“1980年,我在哈佛教书,有一个很出名的中国历史学家的儿子在哈佛念本科,他在学生报上写书评批评我:梁漱溟是个小人物,怎么能跟胡适、毛泽东这些人相提并论?你把他捧成个大人物,他不是。”艾恺笑着说。而事实证明,那个时候“看我书的人越多,梁漱溟的地位就越高了”,“研究梁漱溟的第一人”的头衔也由此而来。 《最后的儒家》出版后不久,艾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梁漱溟曾经的邻居捎来的口信,说梁先生希望能与作者当面讨论。“(能见面)当然兴奋得不得了,但有点紧张、怕。虽然没有见过他的人,我写成相当完整的βroject(论文),有点怕描写错、分析错这个人物。跟他相处几天后,发现自己没有错,心理本来有点不安,后来安了。”艾恺告诉记者。 在北京的第一次见面,艾恺与梁漱溟谈了很多。在之后的两个星期里,艾恺每天一早就到梁漱溟家里。两人分坐一张桌子的两角,桌面搁着的录音机全程记录他们的谈话。2006年1月,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把这个对话整理为单行本《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出版,艾恺说,想不到它会畅销。 “我和哥哥那会主要做些端茶水的工作,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也怕聊太久了对祖父身体不好。”梁漱溟的孙子梁钦宁告诉记者。钦宁的名字是梁漱溟所起,寓意是崇敬列宁。在他眼中,祖父是个很开明的人。他曾问过祖父,“‘文革’抄咱家您生气吗?他回答了三个字,简简单单:不生气。我很奇怪,立刻追问为什么?他说,‘他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他对这些事情看得很淡。” “我近几十年在国外介绍梁漱溟的时候,经常用哲学家的身份。不过我现在觉得应该强调他的另一方面,他最主要的历史上的角色是一个活动家。” 在政治运动中沉浮,在学术之海中跋涉,梁漱溟对自己有独到的认知,1987年,他曾在演讲时说,“总结一生,我不是一个书生,我是个拼命干的人。”这句话讲得很大声,梁漱溟拍着桌子讲。在艾恺眼里,从不囿于书房、坐而论道,是梁漱溟独一无二的地方。 “我近几十年在国外介绍梁漱溟的时候,经常用哲学家的身份。不过我现在觉得应该强调他的另一方面,他最主要的历史上的角色是一个活动家。有点像印度的甘地。在历史上,一提到甘地你会想到他在社会上、政治上的活动,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思想、哲学。”艾恺表示,自己在《最后的儒家》中对梁漱溟作为活动家的评价过低了。 梁漱溟只有中学学历,能成为北大教授,皆因他的论文《究元决疑论》。这篇研究佛学的论文引起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注意,并聘用年仅24岁的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进入北大4年后,1921年,他写下《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学术界一鸣惊人。但他这时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要从繁华的北京去贫苦的农村。“1924年,我头疼,很想离开北大,不同知识分子见面,愿意到乡间去,跟农民生活在一起。我看见了不识字的农民,农民生活太苦。”艾恺回忆梁漱溟生前对他的说法。 乡村建设运动是二三十年代的重要社会运动支流。国家的凋敝引发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忧思,并进而把疗救乡村作为疗救国家的解药和尝试。乡村,被视作乡土中国、现代中国的根本。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领导乡村建设运动,欲以乡村为出发点创造新文化;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欲从扫盲做起改变中国的人民素质;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矢志于推广工商职业教育……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始于1931年,此前他已在广东、河南开展过乡建。虽有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但他不希望这项实验受到省政府太多“关照”,提出了选择实验地点的标准———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社会结构要有代表性,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邹平正合适。 他们在现邹平一中的旧校址处安顿下来,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当时,邹平县城比较小,老一中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城门外边的东关了。在马路北边,有一家卖盐的商店,院子比较大,有十几亩地,是三家合伙的买卖,由于经营不善已经面临倒闭。经过协商,梁漱溟他们买下了这个院子,对房舍简单做了一下装修,然后又在院子里新盖了一座礼堂和七座教室。”邹平一中教师刘庆亮告诉记者。 以后7年里,梁漱溟成立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农场,医院、图书馆、社会调查部和邹平师范学校。每天拂晓,梁漱溟或其他老师都会与学生讲“朝话”,让学生静思。另外,他还成立合作社,教农民种植高产量的棉花,培养出产蛋量高的新鸡,饲养的猪比本地猪重了50斤。 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在他的倡议和主导下成立,棉田面积从1932年的不到900亩,到1934年一下子增加到40000多亩。直到今天,邹平仍然是一个盛产棉花的地区,被列为全国百富县城之一。 梁漱溟的理想是把政府学校化,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要改良,不要用暴力。他有个说法是,“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受伤。”所以要把老百姓与政府的关系改成像师生的关系,艾恺说。 然而,邹平的乡村建设之梦随着日本人的到来,以及军阀韩复渠的逃离而结束。 有学者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失败的,其中最激烈的批评来自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的陈序经,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不过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照搬的是西方的组织方式和科学技术,几乎没有一点纯粹的中国东西。“作为一个标准西化的都市知识分子,他访问邹平归来后得出的结论果然一点也不出人意料:梁漱溟仍然没有能把山东农村变成上海。他以胜利者的口吻指出:邹平的医院缺乏设备而且落后,农居脏得令人恶心,整个邹平找不到一段好一点的公路。”艾恺说。 艾恺也在邹平考察过,他认为梁漱溟的乡建实验是成功的。艾恺做研究有个特点,喜欢搜集一手资料,因为研究梁漱溟,最近20多年他曾到过邹平以及河南省南阳以西的县做研究,也因此关心起中国的乡村建设。 艾恺第一次踏进邹平是1986年。邹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农村窗口,艾恺是最早来到邹平的美国学者之一。随着1985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成立,美国学者在山东邹平进行了长达20多年,多达200多人次的连续性蹲点式的社会研究。 在邹平,艾恺访问了400多位村民。“他们都(把梁漱溟的乡建)赞美到天上去了。”艾恺继续回忆道,“我在村里走,每天都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坐在外面的小凳子上,我过去和她聊天,问她用什么标准分时期?她用吃的东西来划分。大家都记得当时的猪养得很大。30年代多吃点小麦,好像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但是抗战以后,生活水平立刻降低了。” 梁漱溟的名字已经成为邹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73年到现在,艾◇来中国有上百次。看到邹平新修了马路,盖了电影院,老百姓β子好过了,艾◇很欢喜。 80年过去,梁漱溟当年在山东践行的乡村建设运动,至今仍未过时。至近年,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 1996年,廖晓义创立了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 2003年,经济学家温铁军,他秉承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前辈的平民教育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在河北的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任院长。 2007年,李英强、杨民道等人在北京成立立人乡村图书馆,目前在中国多个省份的县级地区已有11个分馆,以促进乡村教育革新为宗旨,开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动。 2011年,广东艺术家欧宁与左靖选定安徽黟县碧山村作为实验基地,邀请各地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当地的工匠、艺人合作,创作出传统工艺和生活用品的当代版,同时举办碧山村和徽州地区历史文献的展览。 10月18日,北京“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廖晓义现身并发言,“梁先生是把我带回家的人,我是他的粉丝。” 廖晓义1986年在中山大学取得哲学系硕士学位,是第一位获得被称为“环保诺贝尔奖”苏菲奖的中国人。1999年,她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农村租了近3000亩山林作为环境教育基地,教农户实行垃圾分类,使用太阳能灯,种植无公害食品,摸索了“生态保护、环境教育、乡村建设、民俗旅游”四位一体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在四川建设了“乐和家园”;2010年,她回到自己的祖籍巫溪,参与了全县的“乐和家园”建设。 “我不是看了梁漱溟先生的书才做乡建,主要是他的思想对我产生重要影响。”廖晓义告诉记者。2000年某天,她读到梁漱溟先生的书,酲醐灌顶,“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前都是从政治上了解他,不关注他在文化层面的思考。他有个重要观点,认为文化失调、失去自己的文化是中国发展的致命点,让我很受启发。另外,他的乡建思想特别了不起,他从乡村上探讨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不以西方思想为目的,引进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 艾恺在2011年参观过廖晓义在重庆巫溪的乡村建设,认为廖的乡村建设活动特别之处在于,是让同村的人感到他们是一体的。这种“一体性”的感受,却正是过去30年中国人正在逐渐失去的,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中国“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原来的社区很难找到真正的社区,大家都住在高楼里,连对门的邻居都不知道,都不认识了”。 外研社编辑付帅曾做过统计,从1973年到现在,艾恺来中国有上百次:1973年来时,中国的公路、建筑物很少,老百姓生活水平不高。1980年来时,感觉到了改革开放的势头,开始出现变化;1982年再来时,就看到了明显的变化;1984年以后更是如此。 看到邹平新修了马路,盖了电影院,老百姓日子好过了,艾恺很欢喜。他追随梁漱溟的脚步踏入了中国的农村,得到的是别样的天地。至于这个国度的未来,艾恺说,可能贫富差距、农民工、环保会是隐患。中国需要观点,但像梁漱溟那样坐而言、起于行,则从未过时。 《梁漱溟文稿手迹选》,梁培宽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78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