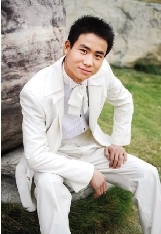|
|||||||||||||||
偷拿美食与小伙伴分享 讲述人:蔡保国 42岁 我小时候那时还是集体劳作。到了过年,村里集体发吃食,一家几棵大白菜,四五个萝卜,分得一小块肥肉。这就是年货了。有的家庭条件好点的就会用粮票换点糖果等小零食。我们家姐妹弟兄七八个,吃的都不够,就更不用说零食了。过年最高兴的就是大姐给做的新衣服,一年可能就那么一件,只有过年那天才舍得穿。 记得有一年过年,在家里的柜子里发现有好吃的,但爸妈不让吃,就偷偷地拿,然后跑到外面的山坡上和小伙伴们集合,在土沟里烧一摊火,然后大家将好吃的都拿出来一起吃。这样就可以吃到多个不一样的好吃食。 那时过年,大部分都是白雪皑皑的天气,我们将秋天捡来的柏树枝拿来烧火取暖。家人围在一起烤火,在煤油灯下,聊聊家常,但却感觉很幸福。 2元压岁钱上缴1元 讲述人:王佳 30岁 我小时候过年最兴奋的是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小时候家庭条件差,那时候过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得到一部玩具——发条小坦克,一拉就可以跑。但家里穷买不起,只能眼巴巴地看村里同龄小伙伴们玩。过年时,我将有2元压岁钱,刚好是一个发条坦克的价钱,心里一直盼着,然而过年了,钱也到手了,但被告知,过完年要上交1元,我当时就蔫了,我的发条坦克又泡汤了。 挨家挨户讨要吃的 讲述:杨广超 25岁 小时候过年,除了会得到爸妈买的新衣服,最期待的就是大年初一那天拿着准备好的袋子到村里各家去拜年讨好吃的东西。为了想装得多,就拿个大袋子,在村里逛一趟,收获满满的,提不动是常有的事。 在1999年大年初一那天,我老早起床了,吵着让妈妈给我穿上已经准备了多时的新衣服。体体面面,绅士极了,梳了头,洗了脸。妈妈端来了饺子,呜哇、呜哇吃完!这时,一对小伙伴已经来我家拜年讨好吃的来了。爸妈拿出了糖果、花生、苹果、甘蔗。吃完饺子,我也加入到他们的拜年队伍,开始拜年旅程。 村子有30多家,一家可得到一把花生、一个苹果、一个橘子、一把糖果。有时还可得到比较稀奇少见的吃食。乐的龇牙笑哈哈,向同龄炫耀自己的收获。然而乐极生悲,摔了一个狗啃屎,呵呵,没事起来继续向下一家出发。半个小时不到,布袋子装满了,使出吃奶的劲将袋子扛回家,将好吃的东西囤积在自己的箱子里,不喜欢的就拿给大家分享。 现在我们都成为城里人了,没有了小时候的那种到各家拜年的习俗,邻里关系变得陌生,家家只是围在自家的电视旁看电视、玩麻将。很怀念那时的美好时光。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提花灯 讲述人:周敏 40岁 小时候过年最高兴的是拿到压岁钱,2元对于现在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在1980年来说应该不算少了,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拿到压岁钱害怕丢了,就紧紧装在兜里,时不时要看一下,要是丢了,可就哭死了。 我们玩得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提花灯了,到了新年,大人们就给孩子做花灯,剪各种好看的纸花、小动物贴在灯笼壁上,红彤彤的灯笼喜气洋洋,小伙伴们也会拿着自己的花灯比哪个好看。一不小心,小伙伴的灯笼蜡烛歪掉了,漂亮的灯笼瞬间化为乌有,哇啊啊!哭得可怜伤心。 过年各种娱乐项目也会竞相上演,舞龙、舞狮、踩高跷。但大部分都是在市集上表演,为了能看到,就长途跋涉去观看。现在这些都没了,感觉好可惜。 “你咋拿这么小的布袋?” 讲述人:王永襄 70岁 1960年进入腊月,眼看就要过年了。那时我17岁,这年春天我从高中到县广播站参加工作,父亲刚刚过世,哥哥、姐姐在外地,家里靠母亲领着两个妹妹在生产队挣工分过活。我是家里的男子汉,过年怎么安排,这个担子我得挑啊!回家和母亲、妹妹们喝了两碗红薯叶杂面条汤,吃了一块饼子,问:“娘啊,这年下马上就要到了,家里都需要啥啊?”“呵呵,傻孩子,这年头,需要啥?生产队全年每人分53斤小麦,年下每人分2两香油,我这儿有安排,再割3斤大肉,也就行了……其他的,还要啥?” 回到县城,我对年货的事一直挂在心头。 到菜市街上转悠,想买点白菜、萝卜什么的,问问都贵得不得了,白菜一元多一斤,红白萝卜也都七八毛一斤——那时物资极端贫乏,公家不经营蔬菜,菜市街“自由市场”上都是卖的高价。 回机关路上遇见我的高中老同学刘宏斌——他是我荥阳高中同班同学,乔楼南边人,高中毕业在家劳动。他个子没我高,但人很机灵,对人总有一颗火热的心。我们相握、相拥,相互拍拍肩膀,那个劲头啊,真比亲兄弟见面还亲…… 老乡加同学,腊月相见当然不能走的。他推脱不过,被我拉到我工作的县广播站,述说了久别之情,该吃午饭了,我们拿上碗筷,来到县委灶房——那时广播站和县委机关同伙吃饭。我买了四个二两的玉米面馍、两碗稀面条,还买了四块方饼干大小的卤豆腐,我说:“我知道你是回民,讲清真,没买肉。”临别,洪斌说:“永襄啊,眼看到过年了,家里都缺啥,言声,别客气。我们生产队临近索河,有水,开有菜园,要不,我给你弄点菜吧?”细细想想,上午赶集看见菜市上那个情景,只得说:“那就弄点白萝卜吧!”我们相约到腊月二十七,我到他家找他。 我去了他家院门,他二话没说,立马下到墙角的红薯窖里,让我在上边拔上来两大篮水灵灵的白萝卜,有的青头处还生有鹅黄鹅黄的嫩芽芽呢!那个年头吃食紧缺,让人看了就心馋。我随手拿出车子上带的白面布袋,他装啊、塞呀,足足装有五六十斤,他还埋怨:“你咋拿这么小的布袋?”他替我推上车子,一直把我送到村口,我走了好远回头看看,我的老同学刘宏斌还在遥遥地向我挥手……顿时,我的心酸楚了,几滴热泪滚滚地掉到车把上…… 我兴冲冲翻沟过河,母亲像接星星似的把我接进大门,老人家脸上乐开了花,高兴地说:“好了、好了,这年下算安置住了!”娘双手摩挲着那白花花的萝卜,说这年头都缺菜,随即给东邻居堂大娘家送去两个,给西邻居金海婶送去两个,还给河东大奶奶家送去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