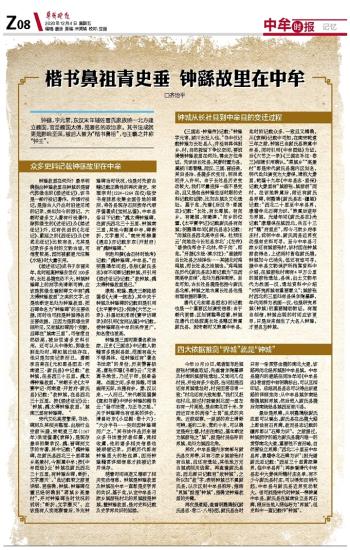|
||||
|
钟繇,字元常,东汉末年辅佐曹氏家族统一北方建立魏国,官至魏国太傅,是著名的政治家。其书法成就更是影响至深,被后人誉为“楷书鼻祖”,与王羲之并称“钟王”。 众多史料记载钟繇故里在中牟 钟繇故里在何处?最早明确指出钟繇故里在钟城的是晋代郭缘生的《续述征记》,该书是一部行役记著作。所谓行役记,是指古人外出时沿途见闻的记录,类似如今的游记。六朝时诸多文人著有行役著作,除郭缘生的《述征记》及《续述征记》外,还有伏滔的《北征记》、戴延之的《西征记》及《宋武北征记》比较有名,尤其是记录许多当时的文物古迹,可信度较高,因而被郦道元注解《水经》时大量引用。 《续述征记》成书于东晋末年,此时距离钟繇去世仅100多年,长社县境变动不大,钟城钟繇碑上的刻字尚清晰可辨,应该是郭缘生看到碑文中有“魏太傅钟繇故里”之类的文字,这是他断定此处为钟繇故里、把石碑命名为“钟繇碑”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可能是钟城得名的主要依据。正因为是郭缘生亲眼所见,又有城和碑两个实物,且碑在“城南三里”,可信度自然极高,被后世诸多史料引用。还可以从中得知,郭缘生到此处时,碑和城已经存在,他只是如实记录而已。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三·尉氏县》中记载:“故钟城,在县西三十五里。魏太傅钟繇故里。”宋朝乐史《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开封府·尉氏县》记载:“故钟城,在县西北三十五里。按《续述征记》云:‘钟城,魏太傅钟繇故里。’城南三里有钟繇碑。 ” 宋代文化高度繁荣,书法、碑刻及其相关整理、出版行业空前兴盛,宋乾道三年(1167年)洪适编著《隶释》,是现存最早的集录汉、魏、晋碑刻文字的专著,其中记载:“魏钟繇碑,在尉氏县西北三十里蒋城乡高兼村,今割属中牟;按《中牟图经》云‘钟城在尉氏西北三十五里,有钟繇古碑,断折,文字磨灭’。”此记载较之前更详细、更准确,钟城、钟繇碑位置已经明确到“蒋城乡高兼村”,并对钟繇碑当时状况的说明:“断折,文字磨灭”。应该是有人实地察看后,补充钟繇碑当时状况,也是对先前古籍记载正确性的再次肯定。宋理宗时(1224~1264在位)临安书商陈思收集全国各地的碑刻,将各县现存石刻按年代顺序编著成《宝刻丛编》,中牟县条目下记载:“魏太傅钟繇碑,在尉氏西北三十五里、钟城南三里,其地今割属中牟,碑断折,文字磨灭。”南宋郑樵著《通志》亦记载东京(开封府)有“魏钟繇碑。” 明赵均撰《金石林时地考》记载:“魏钟繇碑,中牟县。”自明嘉靖年间起,各版《尉氏县志》有不间断记载钟城,并引用《续述征记》记载:“故钟城,魏太傅钟繇故里是已。” 康熙、乾隆、嘉庆三朝陆续编修《大清一统志》,其中关于钟城及钟繇碑的记载则是引用《太平寰宇记》;倪涛《六艺之一录》、孙星衍和邢澍《寰宇访碑录》则引用《宝刻丛编》中记载,使钟繇碑在中牟的流传更广,知名度也更高。 钟繇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正史《三国志》中记载人物籍贯多是到县级,范围有些大不够具体。但钟繇还有“著名书法家”的身份,历来赞誉极高,唐张怀瓘《书断》云:“元常真书绝世,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宋代朝廷编撰《宣和书谱》中评价钟繇的楷书云:“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关于钟繇碑也有很高的评价,清曾衍东《小豆棚·卷十六》:“六分半书……实则因钟繇碑而广之。”其书法作品历来被众多书法爱好者仰慕,竞相收藏,他的诸多相关信息也被顺便记录。历朝历代都有钟繇庞大的粉丝群,因而钟繇籍贯详细信息才能被记录并保存。 随着时间流逝又增添了相关变动信息。钟城是钟繇故里及钟城在中牟一直都是史学界的共识,基于此,认定中牟县刁家乡城前张村北的界城就是钟城,暨钟繇故里,是对史料记载及史学界共识的延续。 钟城从长社县到中牟县的变迁过程 《三国志·钟繇传》记载:“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书中仅记载钟繇为长社县人,并没有具体到乡、村,自然就留下争议空间,要说清楚钟繇故里在何处,需全方位考证。先谈谈长社县,其秦时置为县,属颍川郡管辖,两汉、三国、晋沿袭,其后县治、县境多次变迁,明洪武初并入许州。由于长社县历史变动较大,我们尽量选择一些不易变动,且又是包含钟繇生活时期的史料记载和证物,比如古城及文化遗址。基于此,先看《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长社,有长葛城。有向乡。有蜀城,有蜀津。”向乡的位置,《太平寰宇记》记载尉氏县有向城;明嘉靖年间《尉氏县志》记载:“向城在县西北高寺庄保。杜预注云‘向地在今长社县东北’;《左传》‘诸侯伐郑会于北林,师于向’,即此。”另据《水经·潩水注》:“皇陂即古长社县之浊泽也……其陂北对鸡鸣城,即长社县之浊城也。”鸡鸣城在历代《尉氏县志》都记载为“在西南高寺庄保”,此处为皛泽南岸。至此可知,古长社县境是包括今尉氏县北部,钟城之地古属长社县也是有理有据的事实。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也是一个重要区划演变信息:由于朝代更替、区划调整等因素,钟城在唐代已经脱离长社县辖区转属尉氏县。到宋朝时又转属中牟县,此时的记载众多、一致且又精确。从《隶释》记载中可知,在南宋乾道三年之前,钟城已由尉氏县转属中牟县,同时引用《中牟图经》为证。后《六艺之一录》《三国志补注·卷三》相继引用确认。“蒋城乡”“高兼村”都是宋代尉氏县境内区划名,明代此处演变为大秦保,清称大秦里,乾隆十九年《中牟县志·里保》记载大秦里有“城前张、城前胡”两村。在该地转属后,附近有尉氏县界碑,明嘉靖《尉氏县志·疆域》记载:“西北二十里至中牟县界,康墙寺北石碑为识。”转属后遂呼为界城。光绪年间《尉氏县志》尚记载“康墙保在城西北,共五十三村”辖“府里庄”,即今刁家乡府李庄村,说明中牟、尉氏两县边界变动是有史料可寻。至今中牟县刁家乡还有城前张村,该村因在钟城前故得名,上述两村皆临尉氏境。钟城如今已消失,但还有迹可寻。据中牟县文物保护所档案资料中介绍,在城前张村南有4平方公里的城前张遗址,县保,出土文物年代为战国—汉,遗址资料中介绍“对研究界城有重要意义”;城前张村西北约三里处有县保东陶墓群,年代同样为战国—汉,也是研究界城(钟城)的重要辅助物证。有理由相信,钟城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只是后来诞生了大名人钟繇,才更名为钟城。 四大依据推测“界城”就是“钟城” 今年10月10日,笔者驱车赴城前张村调查取证,先查看东陶墓群及村南的城前张遗址,又询问几位村民,并没有多少收获,当问起是否还有界城遗址时,村民回答非常一致:“村北还有大致轮廓。”我们又赶往村北,刚过村就看到北面一里左右有一片高地,是由南北百十米、东西近百米的两条“土岗”组成的夹角。近前观察,一层层的夯土清晰可辨,高约二米、宽约十米,可以确定是夯土墙,村庄在南边,基本断定为城前张之“城”,就是村民俗呼的界城,此处为城西北角。 其次,中牟县境内东南部与尉氏县交界带,只有刁家乡城前张村有古城,且还有遗址,其他地方无古城或相关线索。再查看尉氏县志,西北部只记载有“故钟城”,之所以加“故”字,表明钟城已不属尉氏县,以示区别中牟县称呼,推测“界城”就是“钟城”,是确定钟繇故里的关键。 再次是道路,查看明嘉靖版《尉氏县志·卷二·八号》图,尉氏县当时只有一条贯穿全境的南北大道,该路再向北经界城到中牟县城。中牟县境内的道路在同治年间《中牟县志》卷首图中有明确标出,可以互相印证。总结两县县志可以得出该道路的详细走向:从中牟县城东南经箜篌城到界城,然后进入尉氏县境后向南绕经县城西至洧川县。 最后是界牌,从明嘉靖版尉氏志里可以看出,尉氏县在出境大路上都设有石界牌,故而县志记载的疆界都以“石牌为识”。之前提过,钟城扼守的路为尉氏县境内唯一的贯穿南北大道,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要设立界牌:“西北二十里至中牟县界,康墙寺北石牌为识”;到光绪尉氏志记载:“西至三十里黄家集界,临中牟县界”;再参看清代中牟县志中大秦保所辖村庄名单,有不少今尉氏县村庄,可以得知自明代起,中牟县与尉氏县边界变动较大。很可能是宋代时钟城一带转属中牟县,尉氏县在城南设立县界石牌,随后当地人随俗呼为“界城”,但史料中一直记载作“钟城”。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