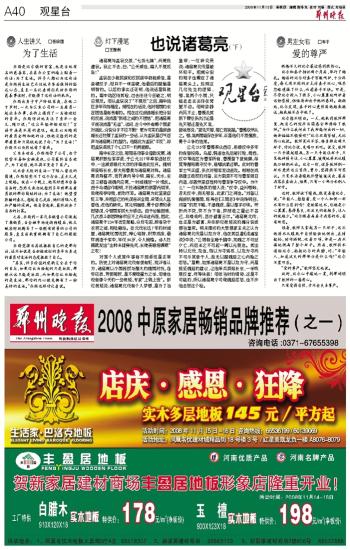□王振洲
诸葛亮与孟获交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孟获在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中都有威信,是条硬汉子,但并不一味蛮硬,他最后的服输是明智的。以后的事实还证明,他说话是算数的。南中地区恃其险,过去往往今日破之,明日复反。但从孟获说了“不复反”之后,南中地区多年保持稳定。用现在的话说,他对蜀国的安定团结是有贡献的。现在这位旅游局长把分裂和反叛,说成是“部落之间的不团结”,把诸葛亮平叛说成是“无道”,试问,古今中外有哪个国家对叛乱、分裂分子不征不剿?更为可笑的是旅游局长还杜撰了孟获的一些话,认为孟获是忍气吞声与诸葛亮订的盟约。他据此为孟获“平反”,却把孟获看成了个心口不一的两面派。
南中安定之后,蜀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诸葛亮积极治军讲武,于公元227年率军进驻汉中,一出威武雄壮大戏的序幕由此拉开。魏明帝亲临长安,派大将曹真与诸葛亮对阵。诸葛亮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而应亮,一时间魏营一片慌乱。由于马谡自作聪明,不按诸葛亮的部署而胡来,致使街亭惨败,前功尽弃。诸葛亮为此呈请自贬三等,并把自己的失误告诉全国,希望众人监督他,改他的缺失。其光明磊落,勇于自责和承担错误,令蜀国军民大为感动。由于运输困难,几次战斗都因粮食供应不上而半途而废,因此,诸葛亮于234年改变策略,分兵屯田,耕者杂于农民之间,相处融洽。在北伐长达7年的时间里,诸葛亮忧国忧民,殚心竭智,积劳成疾,最终病逝于军中,年仅54岁,令人惋惜。诗人杜甫就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叹!
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历史上对诸葛亮北伐有褒有贬,批评者认为,诸葛亮以小国弱民与强大的魏国对抗,连年征战,劳困蜀民,是不度德量力之举,但谁也没有像今天的一些教授、专家“上纲上线”。那位教授说:诸葛亮北伐有个人梦想,是为了当皇帝;一位研究员说:诸葛亮北伐是破坏和平。把闹分裂的帽子也戴在了诸葛亮头上。按照这几位先生的逻辑,蜀、吴两个小国,只能老老实实待在窝里不动。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曹操及其部下曾经多次讨论是先灭蜀还是先灭吴,夏侯淳说:“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曹操欣然从之。蜀、吴两国能存在多年,正是他们不畏强敌,勇于斗争的结果。
公元215年曹操率众西征,称雄汉中多年的张鲁投降。马超、韩遂也先后被打败,陇西、汉中等地区为曹军所有,曹操留下夏候渊、徐晃等强将镇守汉中,高唱凯歌还朝。此时的曹军士气正盛,多次对蜀军发动进攻。刚刚在成都建立政权的刘备,实力简直不可与曹军同日而语,却毅然亲自挂帅与曹军争夺汉中。为什么?一位叫杨洪的蜀人说:“汉中,益州咽喉,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刘备以弱旅抗衡强国,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得明白,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亦避害云尔。”诸葛亮北伐,也正是为避害,并非那位教授说的搞分裂或想当皇帝。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诸葛亮北伐是以攻为守,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说》中说:“公固有全局于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以攻为守而不可示其意于人,故无以服魏延之心而贻之怨怒。”是啊,如果诸葛亮不是以攻为守,而是接受魏延的建议,让他带兵直捣长安,一举恢复汉室,何等快哉!但依当时的情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诸葛亮宁可使魏延怨怒,也不许他去冒这个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