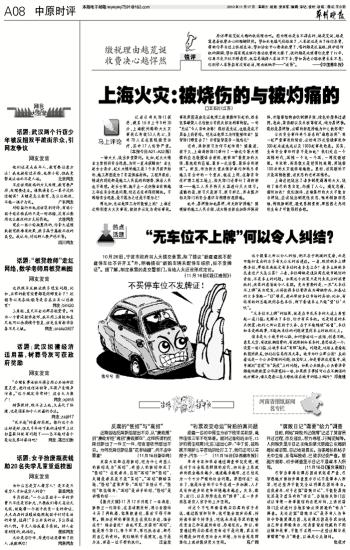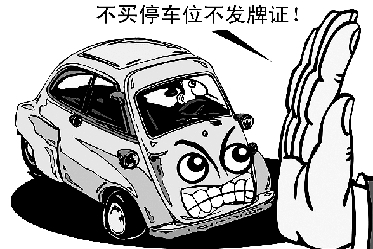10月26日,宁波市政府向人大提交草案,除了提议“新建建筑不配建停车位不许开工”外,明确提出“新购车辆未配停车场所,拟不发牌证”。据了解,制定草案的是交警部门,当地人大还没形成定论。
(11月16日《钱江晚报》)
这个提案之所以令人纠结,倒不在于新规的荒唐,而是可能衍生出的众多有失公允的后遗症。一者,既然新车上牌要车位,那些本来就没有车位的老车怎么办?老车主换新车或者过户又怎么算?二者,车位稀缺是建筑商或城市规划的责任,不是车主的问题。如果这个政策只是约束民众的消费权利,政策的意旨就令人生疑。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无车位不上牌”成为现实,必将使得车位资源成为稀缺珍品,如春运的火车票般一“位”难求,进而带动车位市场的异动:比如,有钱有权的总能找到各色车位,剩下普通车主只能“望‘位’兴叹”。
“无车位不上牌”的结果,就是在市民买车的大道上再竖起一道门槛:先解决了车位,你才有买车权。这是明显的本末倒置:权利之所以区别于义务,在于不能随便“搭售”,车位和车是两码事,不能把车位的问题前置到车主的权利之上。
堵车是大小城市的心病,如何整治这一症结,创意不断、意见无穷,有说收拥堵费的,有说限制私家车的,意思就是一个:设置一些门槛,让城市车流“有限”起来。问题是,这些主意看起来固然很美,但往往容易伤及无辜。城市为什么那么堵?表面看这是一个公共管理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资源过度集中、城市规划“密度”与“高度”上的问题。如果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等都能均衡配置分布得宽松一些,如果很多事情可以在不拥堵的地方解决,谁又愿意心急火燎地堵在城市的路上蜗行?邓海建